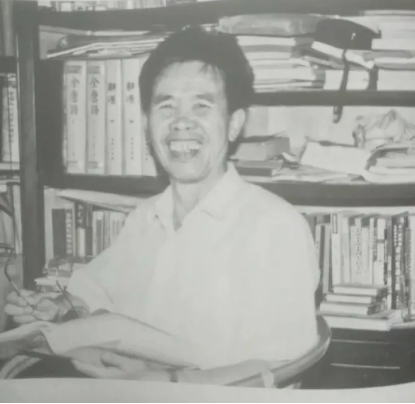
作者韦启良先生
1951年秋天,宜山师范学校(即今宜州民族师范学校)刚刚建立,我有幸成为这所中学校中师第一班的一名学生。说“有幸”,绝非客套,而是实情。那年7月,我在河池中学初中毕业。那时的初中毕业生,也不全都升学 。有的参军参干去,有的做乡村小学老师去了,也有的回乡务农去了。我想继续读书。暑假里我独自去找河池中学陈丹校长。陈校长上过我们班地理课,他认识我。听了我的陈述,他问:你想读高中吗?我说:家里没有钱。他想了一下,又说:那就这样吧,在宜山新成立了一所师范学校,分别到宜山专区各个县招生,河池县要七名,你想考的话,可以到我们学校教导处报名。我觉得他这是真心为我着想的,因而很受鼓舞。于是就依他的指引去报了名。不久即举行考试,考生有三十四名。张榜公布的七名正取生名单上居然也有我的名字。看榜以后,我又一次去见陈校长,向他报告我已被宜山师范学校录取了。他嘱咐我在去宜山上学路过县城的时候,一定要再到他那里去一下。
考取宜山师范的消息,对于我那个开始惴惴不安的家庭,是亦喜亦忧。我家在离县城五六十里的一个偏僻山村里。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知道家里有二十多亩稻田,还有一些山地,常年雇用一个长工,农忙时还请一些短工,每年都有白米出卖,在附近一带算是小有名气的富裕人家。1951年,听说很快就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就给我家的前景带来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引起我父母亲的大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我初中毕业后还能升学,家里自然感到喜出望外。难处也有,虽说师范学校是公费学校,学费、书籍费、伙食费都不用交,但是日常用品、衣物和上学的路费,总还得自备。过去我家的开销,小项靠卖米,大项靠卖牛卖马。那年,村里已成立农会,搞过减租减息运动,我家的财产已经被冻结。经过我自己出面向农会申请,得到许可,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匹大红马,获26万元(旧币,与新人民币的比值是10000:1),13万元给我上学,13万元留给农会。我就带着这笔钱和极简单的行李,步行到县城,去见陈校长。他交给我一封信,要我拿给宜山师范的教导主任。他说宜山师范有他的同学和朋友,我到学校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或问题,他们会关照的。当天,我就由县城坐汽车到金城江,再换乘火车到宜山。
新办的宜山师范学校在宜山县城北门斜对面的山坡上,即现在宜州民师校园的西南角。校舍借用已停办的地委干校的房子,也就是几排草房。学校一边在草房里开学上课,一边在已荒废了的龙江公园(今河池师专校园东头)兴建新校舍。1951年底至1952年初那个寒假,全校学生在罗城参加土地改革宣传工作回来,就住进了一色砖瓦结构的新教室、新宿舍。地委干校原址拨给从城内搬出的宜山高中。那时候的宜山师范只有三个班,即中师第一班、初师第一班和在职教师进修班,合起来也就百把人。以后宜山师范就在这个新校址上发展壮大,直至1978年成为河池师专的中专部,稍后中专部独立设置,恢复宜山师范,才又在原宜山高中校园即原地委干校旧址办学。这就是现在的宜州民族师范。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说出宜山师范这段拐弯抹角的变迁,实在是出于怀旧。我以为我在宜山师范生活的一些旧事,是很值得怀念的。
我入宜师的时候,已近十六周岁,但个头矮小。到地区医院进行新生体检时,我的身高才1.36米。在操场上排队,我是最后一名。在教室里上课,我的座位是第一号。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学号和后来的毕业证书号码都是001。
入学后第二学期,即1952年上半年的一天,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廖政平老师告诉我,学校收到我家乡土改工作队和村农会的公函,说我家的成分已划为地主,要我立即回家,动员父母把埋藏的浮财(主要是金银珠宝)交出来。这个消息使我心里很乱。我知道,我家里饭是够吃有余,存钱是没有,金银珠宝更是无从说起。我回去不仅不会起什么实际作用,倒反很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是不回吗?我显然不能抗拒工作队和农会这份要求。廖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矛盾心情。他安慰似地说:“校领导说了,我们学校是省立而由专区管理的学校,像你这种的问题,得请示专区土改工作总团。”
土改工作总团就在与学校隔河相望的地委大院(今宜州市委驻地)里面。那天,廖老师拿了学校的介绍信,带上我到总团机关。在那里,经由工作人员的引领,我们很快就见到了总团的一位负责干部。班主任递上学校收到的公函,并作了简要说明。那位负责干部边看边听,然后看着我问了一些情况,我拘谨地一一作答。他似乎不假思索地说:“你这么小,懂得什么!回学校读书去。”他又告诉我的班主任:你回去跟你们校长说,你们这回这样处理是对头的;以后还有类似的情况,不管是要学生还是老师回乡,都要报告我们,由我们与下面的工作队联系。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在土改工作总团接见我们的那位负责干部就是总团长贺亦然。他后来做到柳州地委书记、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好像还担任过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副主席。这些都是听说而已,我没有做过查证。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鲜为人知的小事,我心底便油然而生一种敬重和感激之情。我个人绝对是微不足道的的。可是从学校和总团对待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的态度上,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是理性的政策和怎样才算是有政策水平的领导干部。
“回学校读书去。”这句话使我心安,也使我兴奋。我由此而更加喜欢读书。那个年代,学校里有很多直接服务于政治的活动,如上街下乡宣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我一般都参加。老师和同学们也相当看重我在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方面的能力,因此,大凡编黑板报、壁报以至油印小报,以及街头讲演、用铁皮喇叭筒作扩音器念广播稿等等,总有我的一份。但是,我精力的主要投入方面,还是读书。课内的读书,我觉得不难应付。任课的老师们都很敬业。因此我能听懂他们讲的课,能完成他们布置的作业,考试得分一般也不低。
但是,我的读书兴趣更多的是在课外。课外阅读的门道,我走的是两条:一是同学之间的交流、切磋,二是尽可能充分利用图书馆提供的条件。一次,一个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海涛集》好看,真是好看!我去找来看了,一下子觉得眼界大开。那是郭沫若大革命回忆录的一部分,其中写到现代史上许多风云人物。以后一段时间,我几乎读完了当时所能找到的郭沫若的这类著作。后来才知道,这些书是卷贴浩繁的《沫若自传》的一些单行本。由郭沫若的传记,我开始知道创造社、郁达夫和语文课本上“作者简介”以外的鲁迅。所知虽然只是浮光掠影,但我觉得趣味盎然。我后来在专业上倾向现代文学,写作上偏爱传记性的人物札记,大概与宜师时代这种阅读经历有关。这段阅读经历还给我一点启发,即学校教育中除了教师与学生双边活动、双向交流之外,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向交流,也会对一些学生的个性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至于图书馆这个条件,我是利用得比较多的。初创时期的宜山师范图书馆叫做图书室。一间教室半边作书库,半边作报刊阅览室。仅有的一位管理员叫何荣,是一位历史教师的夫人,学生都称她为“何管理员”。她还兼管收发,因而与学生的接触就更多。由于她工作认真,对人态度好,学生都很尊重她。每到下午借还书时间,小书库的一扇窗口面前拥挤不堪,她一个在里面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我问:“我可以帮一下忙吗?”她说:“那就难为你了。”这样,我就有机会进到小书库里面,在她的指导下,做书籍上架下架的劳动,而借书窗口的出纳工作,还是由她来做。日子久了,我对图书室的藏书状况就比较熟悉,哪些书是我要看的,哪些书是我不要看的,我可以先睹为快;平常借书的册数和还期,我可以得到有限的优惠。宜师三年,别的什么长处不敢说,从图书室借阅图书最多的学生中,恐怕也算得上我一个。一直在图书馆工作的“何管理员”早已退休,现在年已八十,但依然行动自如,耳聪目明,精神健旺。几十年来,我都在学校工作,对图书馆一直有一种新近感。这种感情的产生和保持,无疑可以溯源到宜师的读书生活。
将要在宜山师范毕业的时候,我是一门心思准备去做一名小学教师。没想到,教育实习还未结束,学校就通知我和几个同学回来,说是上级有规定,今年要选一部分中师应届毕业生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但只限于报考师范院校;学校决定给我们这几个同学去应考,但鉴于我政治条件方面的先天不足,梁仲彬校长还专门找我个别谈话,有鼓励,有鞭策。我们根据学校要求填表、体检,又回到实习学校去做好实习的结束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于备考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了。这么点时间,全面复习完全不可能,重点复习又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便铁了心:靠平时。那时,桂西北这一片没有考场。我们是到柳州去参加考试的。结果,全班选送九人参加高考,考文科六人全取,考理科三人全落榜。我考取的是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宜山师范按照小学教师的素质要求培养了我三年,我却没有正式做过一天的小学教师。多年以后,我又回到宜山师范学校,做培养小学教师的工作。这来去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得失可言。我最大的所得,是在一些关键的事件上总得到无私的提携和帮助。这些无私的提携和帮助,让我受用终生。为此,我始终不渝地感谢生活,感谢好人。
2001年10月,为宜州民族师范学校建校五十周年作。
【作者简介】韦启良(1935—2005),学者、作家、教授。壮族。广西河池市人。195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曾任河池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今河池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教务处副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著有传记散文集《现代名人母亲》,主编高等学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上下册)。另有随笔、散文、论文多篇见诸报纸杂志。